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谏议注》、卢仝《月蚀诗》、~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谏议注》、卢仝《月蚀诗》、~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谏议注》、卢仝《月蚀诗》、~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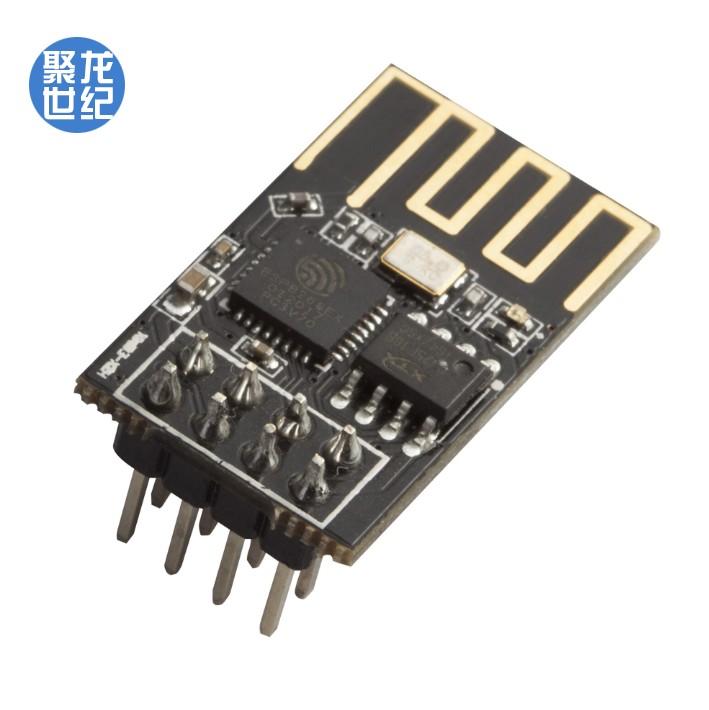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谏议注》、卢仝《月蚀诗》、~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谏议注》、卢仝《月蚀诗》、~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