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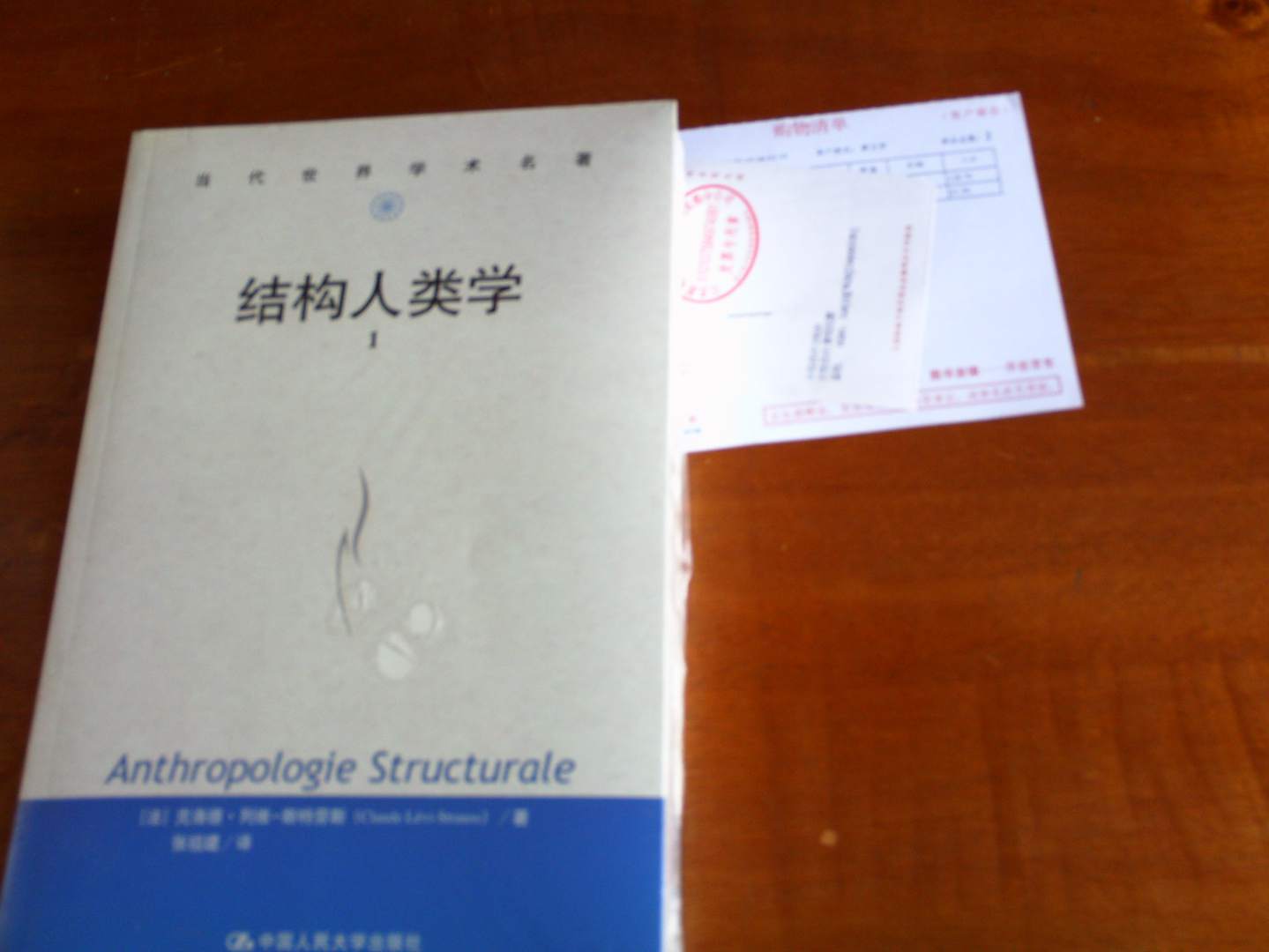 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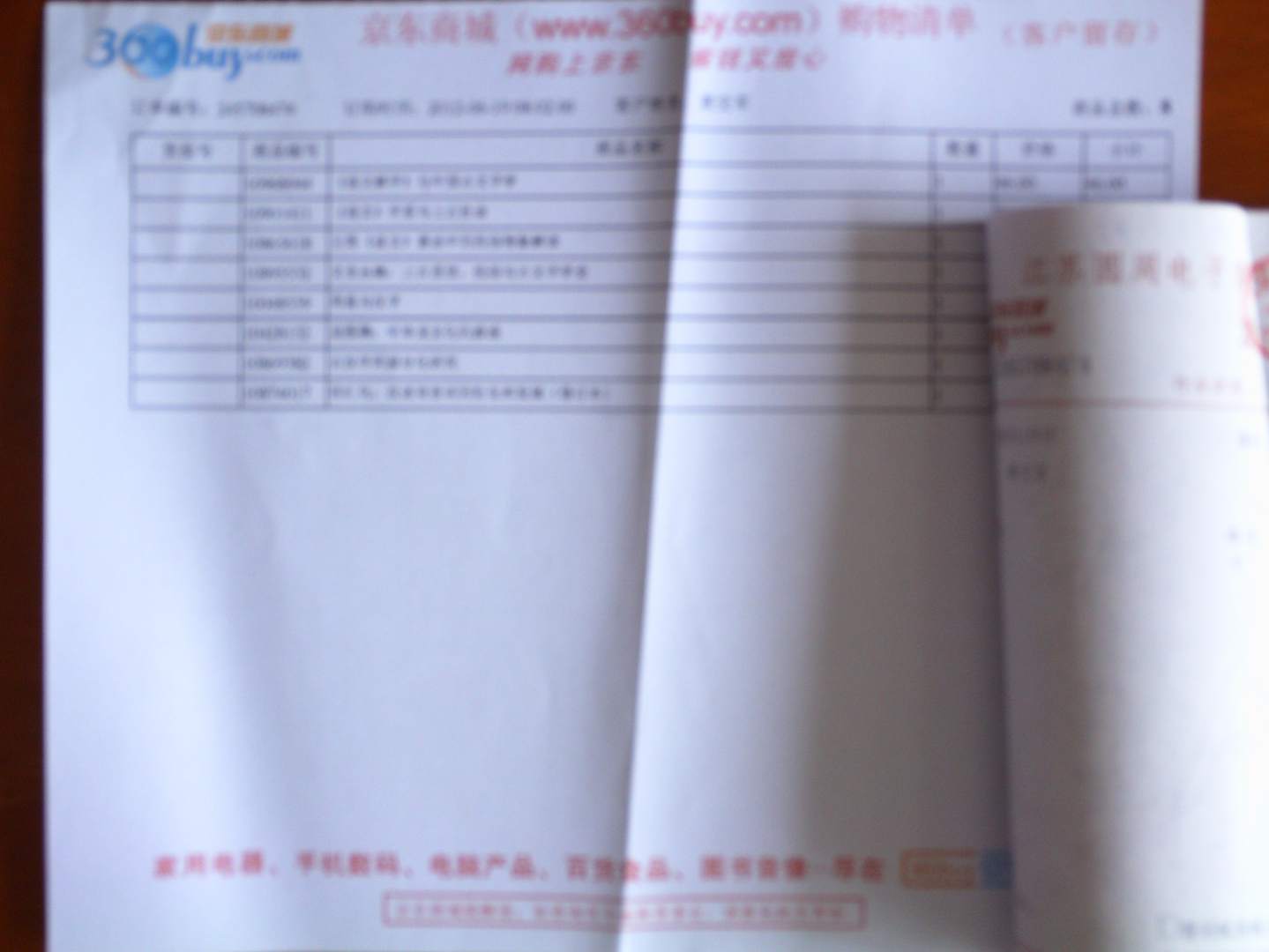 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