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也不想写什么东西,立什么文字,只想感悟其中的一些真道理、真感情。本集子中的两百多则随想录,只是阅读时随手记下的‘顿悟’,并不是‘做文章’。” 作者自序中的这段话,着实让我安心了不少。因为一直很反感所谓的“解梦”式的文字,没错,就是《红楼解梦》那个超长肥皂剧让人倒足了胃口。看多了这些书,估计再看红楼梦就会想玩儿扫雷游戏了,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每个字后面是不会隐藏着什么大关节,大阴谋。诚然脂砚斋同学是说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也认为可能曹老先生在写书的时候会想到一些别的事情而发诸笔端。但是这种事情难道需要那么多人花这么大心血去研究么,而且显然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所谓成果是没有办法证实的,除非曹老先生回魂转世。如果真的这样,也只能是读者之大幸而是红学界的灾难。 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个。看完本书以后,我发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红楼梦的解读方式。 我不否认作者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热爱,不过他好像把这种热爱上升到了某种程度,某种我在从前上学时候在政治课本和教参上能够看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大观园里人物有人是耶稣,有人是佛陀,有人是苏格拉底,甚至有人是日本武士,但就不是一般读者熟悉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本书的益处在于,让你迫不及待的想要重读一遍红楼梦,确认一下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是不是还在那儿,还是已经变成主旋律电影里的皮影了。 可能过度解读是我国的超长文化底蕴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吧,想的太多了,自然就成了毒,非要解不可。让我想起了从小上语文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从一段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里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意思”,更大的副作用在于,一些文章中很明显的“深层”意思,却要伪装成不经意而为之,而且要读者们去费心选择那唯一的答案。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而学生们应该看出来的是:“注意了细节描写。如总理扶正小转椅,这似乎与“一夜的工作”关系不大,但却能表现出总理严谨的思想作风,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估计很多曾经在课堂上分析过这段话的人现在会在心里说 "My ASS!" 要是曹老先生在写红楼梦的时候,确实考虑到我们这些伟大的解读者所解读成果的万分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负责任的宣布他的死因是自己把自己恶心死了? 或者,这些红楼梦的解读者们正在以正面的形式在实践着曹雪芹的教导,“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并且我很奇怪的是,这本书里引用且评论的原文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于程高续本的部分。这倒是一个像当与众不同的地方,只不过,何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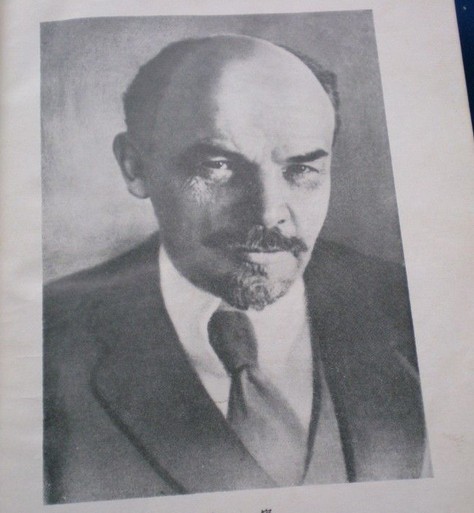 《红楼梦》中有许多共名,也可以说是人物的意象性与类型性的通称,如“梦中人”、“轻薄人”、“大俗人”、“佳人”、“淫人”等,大约不下百余种。有些名称一目了然,有些则寓意很深,更有一些则完全属于曹雪芹,如“槛外人”、“冷人”、“玻璃人”、“卤人”、“富贵闲人”等。作者在百种共名中选定三十种进行解读,开掘人性中更深层次的内容,为读者提供另一个认知人物的视角。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四书”总序自序:人性的孤本梦中人解读 鸳鸯、秦可卿、林黛玉等富贵闲人解读 贾宝玉、贾母等槛外人解读 妙玉、宝玉、林黛玉等卤人解读 贾宝玉、史湘云、香菱等可人解读 秦可卿、晴雯、芳官等冷人解读 薛宝钗、惜春等通人解读 薛宝钗、薛宝琴等玉人解读 黛玉、宝玉、妙玉等泪人解读 林黛玉痴人解读 贾宝玉、林黛玉、尤三姐等正人解读 探春、贾政等真人解读 林黛玉、贾宝玉、晴雯等乖人解读(兼说“妥当人”) 袭人、探春等怯人解读 迎春、秦钟等愚人解读 夏金桂、贾瑞等能干人解读 王熙凤、探春等玻璃人解读 王熙凤等明白人解读 平儿颖悟人解读 宝玉、柳湘莲、紫娟、贾雨村等知音人解读 贾宝玉、林黛玉等冷眼人解读 冷子兴、秦可卿、惜春等伶俐人解读 小红、贾芸等糊涂人解读 史湘云、贾宝玉等读书人解读 贾政、贾宝玉等滥情人解读 贾琏、薛蟠等嫌隙人解读 赵姨娘、邢夫人、夏金桂等尴尬人解读 贾赦等势利人解读 封肃、娈童师傅等小人解读 赵姨娘等废人解读 薛蟠等浊人解读 贾蓉等
《红楼梦》中有许多共名,也可以说是人物的意象性与类型性的通称,如“梦中人”、“轻薄人”、“大俗人”、“佳人”、“淫人”等,大约不下百余种。有些名称一目了然,有些则寓意很深,更有一些则完全属于曹雪芹,如“槛外人”、“冷人”、“玻璃人”、“卤人”、“富贵闲人”等。作者在百种共名中选定三十种进行解读,开掘人性中更深层次的内容,为读者提供另一个认知人物的视角。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红楼四书”总序自序:人性的孤本梦中人解读 鸳鸯、秦可卿、林黛玉等富贵闲人解读 贾宝玉、贾母等槛外人解读 妙玉、宝玉、林黛玉等卤人解读 贾宝玉、史湘云、香菱等可人解读 秦可卿、晴雯、芳官等冷人解读 薛宝钗、惜春等通人解读 薛宝钗、薛宝琴等玉人解读 黛玉、宝玉、妙玉等泪人解读 林黛玉痴人解读 贾宝玉、林黛玉、尤三姐等正人解读 探春、贾政等真人解读 林黛玉、贾宝玉、晴雯等乖人解读(兼说“妥当人”) 袭人、探春等怯人解读 迎春、秦钟等愚人解读 夏金桂、贾瑞等能干人解读 王熙凤、探春等玻璃人解读 王熙凤等明白人解读 平儿颖悟人解读 宝玉、柳湘莲、紫娟、贾雨村等知音人解读 贾宝玉、林黛玉等冷眼人解读 冷子兴、秦可卿、惜春等伶俐人解读 小红、贾芸等糊涂人解读 史湘云、贾宝玉等读书人解读 贾政、贾宝玉等滥情人解读 贾琏、薛蟠等嫌隙人解读 赵姨娘、邢夫人、夏金桂等尴尬人解读 贾赦等势利人解读 封肃、娈童师傅等小人解读 赵姨娘等废人解读 薛蟠等浊人解读 贾蓉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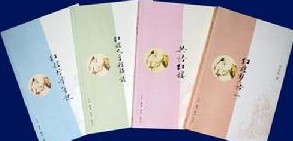 “此外,也不想写什么东西,立什么文字,只想感悟其中的一些真道理、真感情。本集子中的两百多则随想录,只是阅读时随手记下的‘顿悟’,并不是‘做文章’。” 作者自序中的这段话,着实让我安心了不少。因为一直很反感所谓的“解梦”式的文字,没错,就是《红楼解梦》那个超长肥皂剧让人倒足了胃口。看多了这些书,估计再看红楼梦就会想玩儿扫雷游戏了,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每个字后面是不会隐藏着什么大关节,大阴谋。诚然脂砚斋同学是说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也认为可能曹老先生在写书的时候会想到一些别的事情而发诸笔端。但是这种事情难道需要那么多人花这么大心血去研究么,而且显然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所谓成果是没有办法证实的,除非曹老先生回魂转世。如果真的这样,也只能是读者之大幸而是红学界的灾难。 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个。看完本书以后,我发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红楼梦的解读方式。 我不否认作者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热爱,不过他好像把这种热爱上升到了某种程度,某种我在从前上学时候在政治课本和教参上能够看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大观园里人物有人是耶稣,有人是佛陀,有人是苏格拉底,甚至有人是日本武士,但就不是一般读者熟悉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本书的益处在于,让你迫不及待的想要重读一遍红楼梦,确认一下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是不是还在那儿,还是已经变成主旋律电影里的皮影了。 可能过度解读是我国的超长文化底蕴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吧,想的太多了,自然就成了毒,非要解不可。让我想起了从小上语文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从一段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里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意思”,更大的副作用在于,一些文章中很明显的“深层”意思,却要伪装成不经意而为之,而且要读者们去费心选择那唯一的答案。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而学生们应该看出来的是:“注意了细节描写。如总理扶正小转椅,这似乎与“一夜的工作”关系不大,但却能表现出总理严谨的思想作风,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估计很多曾经在课堂上分析过这段话的人现在会在心里说 "My ASS!" 要是曹老先生在写红楼梦的时候,确实考虑到我们这些伟大的解读者所解读成果的万分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负责任的宣布他的死因是自己把自己恶心死了? 或者,这些红楼梦的解读者们正在以正面的形式在实践着曹雪芹的教导,“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并且我很奇怪的是,这本书里引用且评论的原文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于程高续本的部分。这倒是一个像当与众不同的地方,只不过,何必呢?
“此外,也不想写什么东西,立什么文字,只想感悟其中的一些真道理、真感情。本集子中的两百多则随想录,只是阅读时随手记下的‘顿悟’,并不是‘做文章’。” 作者自序中的这段话,着实让我安心了不少。因为一直很反感所谓的“解梦”式的文字,没错,就是《红楼解梦》那个超长肥皂剧让人倒足了胃口。看多了这些书,估计再看红楼梦就会想玩儿扫雷游戏了,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每个字后面是不会隐藏着什么大关节,大阴谋。诚然脂砚斋同学是说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我也认为可能曹老先生在写书的时候会想到一些别的事情而发诸笔端。但是这种事情难道需要那么多人花这么大心血去研究么,而且显然易见的是,这些研究的所谓成果是没有办法证实的,除非曹老先生回魂转世。如果真的这样,也只能是读者之大幸而是红学界的灾难。 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个。看完本书以后,我发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红楼梦的解读方式。 我不否认作者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热爱,不过他好像把这种热爱上升到了某种程度,某种我在从前上学时候在政治课本和教参上能够看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大观园里人物有人是耶稣,有人是佛陀,有人是苏格拉底,甚至有人是日本武士,但就不是一般读者熟悉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本书的益处在于,让你迫不及待的想要重读一遍红楼梦,确认一下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是不是还在那儿,还是已经变成主旋律电影里的皮影了。 可能过度解读是我国的超长文化底蕴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吧,想的太多了,自然就成了毒,非要解不可。让我想起了从小上语文课,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从一段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里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意思”,更大的副作用在于,一些文章中很明显的“深层”意思,却要伪装成不经意而为之,而且要读者们去费心选择那唯一的答案。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进后面去了。”而学生们应该看出来的是:“注意了细节描写。如总理扶正小转椅,这似乎与“一夜的工作”关系不大,但却能表现出总理严谨的思想作风,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估计很多曾经在课堂上分析过这段话的人现在会在心里说 "My ASS!" 要是曹老先生在写红楼梦的时候,确实考虑到我们这些伟大的解读者所解读成果的万分之一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负责任的宣布他的死因是自己把自己恶心死了? 或者,这些红楼梦的解读者们正在以正面的形式在实践着曹雪芹的教导,“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并且我很奇怪的是,这本书里引用且评论的原文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于程高续本的部分。这倒是一个像当与众不同的地方,只不过,何必呢?